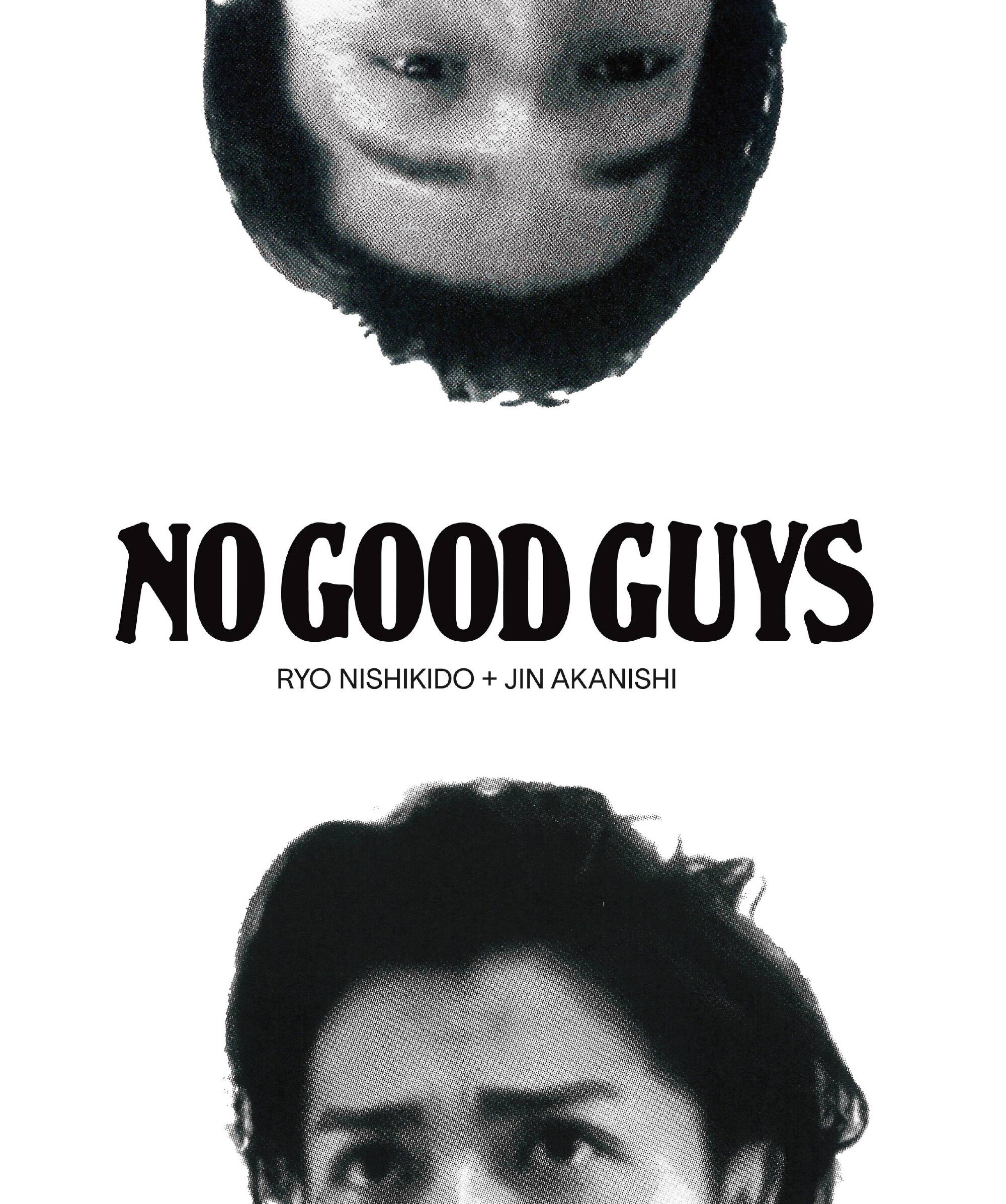正念或者冥想其实是一个行为训练
看到俊煜昨天的通讯,「不管用什么方法划分四季,都不能否认 —— 北京的秋天已经到了」。说不定很快也会过去了。在 temp 的待写文章列表越来越长。最后变成了很多条推特或者即刻。
跟自己说了声抱歉,两个月前就停下工作了。
也很好笑,受疫情影响办公室也没开,所有的手续都在微信、workday、邮件和 slack 上完成了。虽然好久没听到有人在谈论「数字原住民」的概念了,兴许大家都接受了(?)。但这其实也有点刻奇 —— 因为受疫情影响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方方面面的。但真实落在自己身上的小事上,竟然只想得起五年前《IT 公论》。回到日常,预设自己会花很多时间在家冲浪。但更多时间还是待在咖啡店和烤串店。甚至终于扭扭捏捏地搬了家。
天气突然就变凉了,和「北京的秋天已经到了」一样。帮我做常规理疗的大夫进藏了,停诊前她问了我要不要跟她一起,去藏区待着。我说不了我摆脱不了我的世俗日常。
民间对待宗教的态度一直秉持骨子里的中庸:不可不信,不可全信。
李银河在《一个无神论者的静修》里谈及「世俗修行」:「人活着有各类欲望,食欲和性欲是其中最重要的欲望。节制食欲和性欲,就可以获得内心的的平静,但是并没有身体喜乐在其中。精神上的喜乐需要完全的随心所欲,自由自在,自由奔放。」
但训练「精神自由」并不容易。
Skinship(查了翻译是「肌肤之亲」,觉得并不是合适的语境)是很重要的,爱人同床不一定是性关系,而是身体接触。停止理疗之后,练习正念或是冥想似乎真的变成了一个行为训练。有时候出了神或者开始犯困,或者是变得更加疲倦。Medication 和 Meditation 就差了一个字母,前者在治疗身体,后者在训练大脑。我做的练习其实很简单,不需要去回顾或者分析,把它包起来扔到流水线上就好。有时候没包好,再捡起来包一次就是了。
创伤和愤怒并不需要被咀嚼。该食食,该色色,只是摒弃过分的欲望。当然,仍旧只是象征意义上的。再高阶的方法论、咨询、酒饮,甚至药物恐怕都难以给予一个答案。毕竟「独立做决定」是很多人的难处。我是没法帮你做决定的,我是没法像你一样了解你自己的。
同理心是很疼痛的,跟一个人感同身受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地去理解她/他,你需要蹲下来,聆听和沟通。对于更多人来说,能共处就好。即便可以非常深刻地理解一个人的选择、价值判断或者行为,那是想通了「哦你是这样想的」而不是产生了共鸣。
傍晚经常下雨,待在北京就一直挺好的。